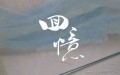潮州筝八讲之六《秋思》 潮州筝八讲之六 一、《秋思》的前世今生 ①外江曲入粤之潮化和客化 《秋思》前身是“外江曲”《过江龙》,所谓“外江曲”是指清道光年间从安徽、湖南一带流入潮汕的乐曲 ( 先普宁,后潮州,再汕头 ) 经潮州乐人潮化而为潮州汉调,是潮州音乐六大品种之一。“外江曲”沿东江上山落户大埔、梅州就叫客家汉乐。“外江曲”《过江龙》由潮州乐人四度移位,易“5”为“2”,易名《反江龙》,这是《秋思曲》 的前世。 (“外江”是潮汕民间对于长江沿线各省份的统称。) ②从《过江龙》→《反江龙》→《秋思曲》→《秋思》(三调)的流变。 《过江龙》因四度移位演奏,老辈人易名为《反江龙》,以示区别。后来又恢复《过江龙》的曲名。《过江龙》易名《秋思曲》始于郭鹰先生,郭鹰先生传谱的重六调《秋思曲》在上海音乐学院定谱、定指法,得到标准、规范的传承,出版发行了范上娥、王昌元等老师的唱片在筝坛得到广泛的传播,上海筝会还将郭先生传播的《秋思曲》列为五级考级曲目。 2016 年 9 月,我应邀到上海音乐学院讲学,将《过江龙》改编成《秋思》( 三调连奏 ) 一曲三调,赋予乐曲新的音乐内涵。通过 20 板小曲的演示,学生较直观地了解源于二四谱的潮乐轻、重、轻三重三调自然互换和潮筝的体系性技法的安排。 二、体系性技法 对于外地筝友来说,《秋思》三调连奏这首曲难在潮州筝左手做韵技巧,这是学习《秋思》的重难点: 1.轻揉连吟 音韵连接 2.揉 前后推拉 3.揉滑 揉滑连音 4.弹弦滑 同弦做韵 5.#3 加重吟 源于活五 6. 上下滑连音 斜线按弦 7. 一指点滑 轻巧快速 8.“4”的做韵 活奏与死按 三、《秋思》三调连奏对秋天自然景色的描绘、遐思和技法安排 从这首《秋思》三调连奏,我们可以看到潮州筝各调对“6、3”和“7、4”的做韵特点。 第一段 重三六调。节奏慢缓,以繁复多变的按音技法,情深韵浓,描绘秋风落叶的悲凉气息和伤感。 第 1 小节的“弹弦滑”。从中辨识潮州筝对轻六、重六按音手法的定位;海派潮筝与本土潮筝做韵的不同。 第 2 小节第二拍的“揉”。 第 3 小节的“4”的演示,外地经常按音不到位。用潮州音乐术语叫作“退徽”。 第 4 小节。强调潮筝花指;“6”的吟音;“4、6”的换指按弦;“4#3”的做韵,突出伤感。 吟:(颤音):潮律与力度。 揉滑 :先揉后滑。 攥: 突出抹指的板音。 上下滑连音:创新技法,潮筝技法与河南技法融合。 第 18—19 小节,三个“7”上滑连吟的钢弦筝奏法。 第二段 轻三重六调 轻六、重六的复合调但偏于轻六,表现秋菊傲放,婀娜多姿的情景,其中的“4”是色彩音,其按音技法介于轻六、重六之间,比轻六略硬,以死按为主。 4 的按音做韵 轻三重六调中,“4”这个色彩音的按音做韵的原则是:除标注技法之外,(比如第 10 小节的“4”揉滑 ) 一般用轻六调的手法——死按或轻吟。 “6”的下滑音,手法宜轻,稍按,触弦的同步回放,未达空弦即按住。 第三小节“2 4 2 1 6 1”的“6”(下滑)音未到,音先到,应指从容, 可用单指按弦。单指按音是高哲睿先生创立的分按弦技法之一,强调单指头的独立和灵活,使按音更从容,更有韵味。 第 14 小节的“6、1”,“6”的轻揉要使与“1”音韵连接。 第 15 小节“6”的波音运指的“快”与“灵” 第三段 轻六调 表现秋收时节,稻谷飘香的场面。按音手法宜轻、快、灵,在造句方面用潮乐的加花手法,以突出欢悦,愉快的气氛。 1.乐句的加花,使音乐轻快、活泼。( 比较古谱与本版筝谱 ) 2.花指。第一个花指刮二根弦。 3.轻下滑、轻吟的(第 1 小节到第 6 小节)和第 15 小节的波音,按弦要灵活主动,掌握好“小”“快”“灵”的按音运指和轻巧的着弦右手技法。 4. 第 18—19 小节“666”轻揉、轻吟的音韵连接。 第四段 推奏 推奏是轻六调的乐句加花变奏,三点一、撮指四点一、切分推,过板推穿插乐段之间,最后高音区减字轻吟,放慢节奏,结束全曲。 (《筝韵问渡》P205~207)